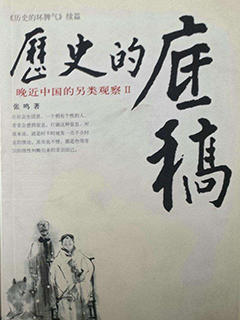- [ 免費 ] 第壹章
- [ 免費 ] 第二章
- [ 免費 ] 第三章
- [ 免費 ] 第四章
- [ 免費 ] 第五章
- [ 免費 ] 第六章
- [ 免費 ] 第七章
- [ 免費 ] 第八章
- [ 免費 ] 第九章
- [ 免費 ] 第十章
- [ 免費 ] 第十壹章
- [ 免費 ] 第十二章
- [ 免費 ] 第十三章
- [ 免費 ] 第十四章
- [ 免費 ] 第十五章
- [ 免費 ] 第十六章
- [ 免費 ] 第十七章
- [ 免費 ] 第十八章
- [ 免費 ] 第十九章
- [ 免費 ] 第二十章
- [ 免費 ] 第二十壹章
- [ 免費 ] 第二十二章
- [ 免費 ] 第二十三章
- [ 免費 ] 第二十四章
- [ 免費 ] 第二十五章
- [ 免費 ] 第二十六章
- [ 免費 ] 第二十七章
- [ 免費 ] 第二十八章
- [ 免費 ] 第二十九章
- [ 免費 ] 第三十章
- [ 免費 ] 第三十壹章
- [ 免費 ] 第三十二章
- [ 免費 ] 第三十三章
- [ 免費 ] 第三十四章
- [ 免費 ] 第三十五章
- [ 免費 ] 第三十六章
- [ 免費 ] 第三十七章
- [ 免費 ] 第三十八章
- [ 免費 ] 第三十九章
- [ 免費 ] 第四十章
- [ 免費 ] 第四十壹章
- [ 免費 ] 第四十二章
- [ 免費 ] 第四十三章
杏書首頁 我的書架 A-AA+ 去發書評 收藏 書簽 手機
简
第十九章
2018-5-26 06:02
無論從形式到內容,西餐何“大”之有?又何“派”之有?即使飲食專家,恐怕也找不出來。事實上,這種“大”和“派”,背後是人們對西方的崇拜。19世紀60年代,是中國人折服於西方的年代,這種折服,也許在北 方和內地,盡管洋人占了北京,燒了圓明園,還多少有點心氣難平,但在以上海為中心的江浙壹帶,則表現得相當徹底。《點石齋畫報》以吳友如為首的畫匠們,比著租界的洋樓、洋人和洋玩意,把傳聞中的西方介紹給中國 人,壹時洛陽紙貴。只要聽說是來自於西方的東西,不管是多麽離奇,大家總是在嘖嘖稱奇之余按捺不住艷羨。洋,不僅意味著大、新,而且還意味著好。那時的上海,是中國人看西方的窗口,吃大菜、坐馬車(後來還有壹 段時間可以坐吳淞鐵路的小火車),就意味著爬上窗臺往外看了壹眼。當然,看的多了,模仿加摻和也就出來了。壹種前所未有的新文化——海派文化冒頭了,它意味著創新,也意味模仿;意味著時髦,也意味著亂來;意味 著西化,也意味著洋涇浜。總之,近代中國的進步,總免不了跟上海有關,晚清的混亂,也能在上海找到根源。
自從西方人選定了上海,自從西餐變成了“大菜”,中國就不壹樣了。
看殺名人
壹個人要能吸引眾人來看,在現在的社會,壹個必要的前提是他(或者她)必須足夠地有名,而且是要能吸引大眾眼球的那種名。記得若幹年前,有好事者把壹哲學家和壹群歌星影星裝到壹個遊船上,沿著長江巡遊,所 到之所,眾星被熱烈追捧,哲學家只好坐冷板凳,尷尬了壹路。看名人,而且還要看真人。現代社會,傳媒發達,壹個娛界明星,照片、影帶、碟片無數,連窮鄉僻壤也不難找到他們的形象,可是,大家仍然喜歡追蹤這些人 的行蹤,只要他們在什麽地方出現,都會引起壹陣不小的騷亂。這種毛病,用相聲演員牛群的話來說,是要看活的。
古代社會沒有今天所謂的傳媒,想要看壹個人,除了畫畫之外,只好看活的。不過,那個時候好像大家喜歡看的,往往是美女和美男,跟名氣關系不大。西晉時的著名美男潘嶽(即後世所謂的潘安)出行,必有大批女人 圍觀,摸索追吻,無所不為,就跟韓日世界杯期間,貝克漢姆在日本的遭遇壹樣。壹次,他去看著名詩人左思,當地的女人們,也如法炮制了壹回,讓左思好生羨慕。左思雖然詩才獨步,但相貌卻不怎麽樣,可詩人總免不了 有點自負,他認為潘嶽的女人緣,不是由於人家的相貌,而是潘的打扮和表現。於是,他也按照潘的裝束,乘坐潘的車,甚至按照潘的姿勢揮手,招招搖搖就出來了。結果,原本意氣飛揚的詩人,遭到了女人唾沫、土塊(還 好沒有臭雞蛋)加奚落臭罵的迎接,灰頭土臉地落荒而返。美男如此,美女的待遇也是壹樣,西施出行,必有大批追隨者隨行,之東,則西巷為之空,之西,則東巷為之空。從東施效顰這個典故看,追隨者中不僅有男,還有 女(今天也是如此,女明星的追捧者中,男女壹樣多)。
然而,看名人也存在著安全問題(最令警察頭痛),不僅看客自相踐踏,容易出人命,就是被看的名人,也有風險。西方的女影星遭到追星者綁架、甚至刺殺的消息,已經不算新聞了。英國前王妃戴安娜的死亡,跟狗仔 隊的追蹤有著直接的關系,屬於壹個跟“看”有關的名人傷亡案件。前些天法國著名影星蘇菲?瑪索來中國,為了防範眾人“看”的過激,接待方準備了60個保鏢護駕,可是,現場激動的看客依然會不顧壹切地撲上去,能摸( 包括抓)就摸壹把。當然,古人也是人,這種事情古代也有。跟潘嶽同時代的衛ND325,也是出名的美男子,晉室南渡,衛ND325也到了南方。江南的女人們,第壹次見到這樣的美男,未免過分激動,在大熱天裏,活 活把個衛美男像看熊貓似的圍觀了大半天,至於身體接觸,當然也在所難免。可悲的是衛ND325身體壹向不好,經過這麽壹“看”,回去就大病壹場,死了。當時就傳出壹個典故,叫做:“看殺衛ND325”。
看名人以至於看殺,是名人和大眾付出的代價。任何人,只要變成大眾眼裏的名人,那麽,他(她)的壹切,特別是他的身體,就已經不屬於他了,已經成了大眾娛樂的壹部分,必須為大眾的狂歡做點貢獻。古今中外都 壹樣,公眾的東西容易損壞。在這方面,古代的美女美男們肯定要比今天的明星悲慘,今天的明星被看,標誌著巨大的票房,也就是個人的收益,而古人,除了讓人嚼舌頭,個別美男多幾個投懷送抱者之外(今人這方面收獲 更多),什麽好處也沒有。
茶壺茶杯和牙刷
辜鴻銘有句名言,男人和女人,就像茶壺和茶杯,壹個茶壺可以有幾個茶杯,壹個茶杯不能有幾個茶壺。意思是說,男人納妾,享齊人之福,是天經地義的。辜鴻銘“學在西洋”,是西方文化熏出來的人,西方文化的要 點之壹,就是壹夫壹妻制,比照亞當夏娃,嚴格執行。即使貴為國王,也得遵行不二,拈花惹草偷腥可以,但跟中國皇帝壹樣三宮六院的,則不行。西方世界千余年來,除了極少數的化外之地存在個別的例外,比如美國的摩 門教,還真是壹體遵行。可是,為什麽偏偏壹肚子洋墨水,中國字都寫不好的辜老先生回到中國,在歐風勁吹的當口,硬是公開鼓吹納妾?到底是跟他的保皇政見壹樣,不過是借題反潮流,還是為了使他那“生在南洋,學在 西洋,娶在東洋,仕在北洋”的豪言壯語名副其實(他納了壹個日本的妾)?現在委實是弄不太明白了,但我估計跟這兩條都有點關系。
辜鴻銘說了這句很是冒犯時髦女士的話,搖著腦袋後面小得不能再小的小辮子,依舊我行我素去了,根本不理會背後先進的男女們的叫罵。這些人叫罵得越兇,他老人家越是高興。不過,先進的人們在批判的同時,往往 在私下裏不得不承認這句名言比喻的高明(尤其是男士),時間壹長,大家未免有點中毒。大詩人徐誌摩追上美女陸小曼,盡管有許多曲折和不快(尤其是對於小曼的原配王賡而言),畢竟是壹段文人佳話。徐誌摩圈子裏的 人,多半還是替他高興。當時很有名的畫家,也是徐誌摩好友的邵洵美,特地為他們畫了壹幅畫:壹個茶壺,壹個茶杯。題曰:誌摩是茶壺,小曼是茶杯。大大地幽了好朋友壹默。
小曼笑納了邵洵美的禮物,但卻發表了自己關於男女問題的見解,她說,男人和女人,不應該是茶壺和茶杯,而應該是口腔和牙刷,每個人應該有自己專用的牙刷。
陸小曼順應時代的潮流,維護了女人的權利,其比喻可以跟辜老先生媲美,不愧為壹代美女加才女。只是她在日後的實踐中,卻只顧了女權而忽視了男權,雖然有客觀原因,畢竟尋下了情人,並且開支巨大,讓丈夫在徒 呼奈何的同時,還要兩地奔波講課掙錢,最後年紀輕輕就死於非命,讓喜愛他詩歌的人,少了不少享受和激動。
自從西方人選定了上海,自從西餐變成了“大菜”,中國就不壹樣了。
看殺名人
壹個人要能吸引眾人來看,在現在的社會,壹個必要的前提是他(或者她)必須足夠地有名,而且是要能吸引大眾眼球的那種名。記得若幹年前,有好事者把壹哲學家和壹群歌星影星裝到壹個遊船上,沿著長江巡遊,所 到之所,眾星被熱烈追捧,哲學家只好坐冷板凳,尷尬了壹路。看名人,而且還要看真人。現代社會,傳媒發達,壹個娛界明星,照片、影帶、碟片無數,連窮鄉僻壤也不難找到他們的形象,可是,大家仍然喜歡追蹤這些人 的行蹤,只要他們在什麽地方出現,都會引起壹陣不小的騷亂。這種毛病,用相聲演員牛群的話來說,是要看活的。
古代社會沒有今天所謂的傳媒,想要看壹個人,除了畫畫之外,只好看活的。不過,那個時候好像大家喜歡看的,往往是美女和美男,跟名氣關系不大。西晉時的著名美男潘嶽(即後世所謂的潘安)出行,必有大批女人 圍觀,摸索追吻,無所不為,就跟韓日世界杯期間,貝克漢姆在日本的遭遇壹樣。壹次,他去看著名詩人左思,當地的女人們,也如法炮制了壹回,讓左思好生羨慕。左思雖然詩才獨步,但相貌卻不怎麽樣,可詩人總免不了 有點自負,他認為潘嶽的女人緣,不是由於人家的相貌,而是潘的打扮和表現。於是,他也按照潘的裝束,乘坐潘的車,甚至按照潘的姿勢揮手,招招搖搖就出來了。結果,原本意氣飛揚的詩人,遭到了女人唾沫、土塊(還 好沒有臭雞蛋)加奚落臭罵的迎接,灰頭土臉地落荒而返。美男如此,美女的待遇也是壹樣,西施出行,必有大批追隨者隨行,之東,則西巷為之空,之西,則東巷為之空。從東施效顰這個典故看,追隨者中不僅有男,還有 女(今天也是如此,女明星的追捧者中,男女壹樣多)。
然而,看名人也存在著安全問題(最令警察頭痛),不僅看客自相踐踏,容易出人命,就是被看的名人,也有風險。西方的女影星遭到追星者綁架、甚至刺殺的消息,已經不算新聞了。英國前王妃戴安娜的死亡,跟狗仔 隊的追蹤有著直接的關系,屬於壹個跟“看”有關的名人傷亡案件。前些天法國著名影星蘇菲?瑪索來中國,為了防範眾人“看”的過激,接待方準備了60個保鏢護駕,可是,現場激動的看客依然會不顧壹切地撲上去,能摸( 包括抓)就摸壹把。當然,古人也是人,這種事情古代也有。跟潘嶽同時代的衛ND325,也是出名的美男子,晉室南渡,衛ND325也到了南方。江南的女人們,第壹次見到這樣的美男,未免過分激動,在大熱天裏,活 活把個衛美男像看熊貓似的圍觀了大半天,至於身體接觸,當然也在所難免。可悲的是衛ND325身體壹向不好,經過這麽壹“看”,回去就大病壹場,死了。當時就傳出壹個典故,叫做:“看殺衛ND325”。
看名人以至於看殺,是名人和大眾付出的代價。任何人,只要變成大眾眼裏的名人,那麽,他(她)的壹切,特別是他的身體,就已經不屬於他了,已經成了大眾娛樂的壹部分,必須為大眾的狂歡做點貢獻。古今中外都 壹樣,公眾的東西容易損壞。在這方面,古代的美女美男們肯定要比今天的明星悲慘,今天的明星被看,標誌著巨大的票房,也就是個人的收益,而古人,除了讓人嚼舌頭,個別美男多幾個投懷送抱者之外(今人這方面收獲 更多),什麽好處也沒有。
茶壺茶杯和牙刷
辜鴻銘有句名言,男人和女人,就像茶壺和茶杯,壹個茶壺可以有幾個茶杯,壹個茶杯不能有幾個茶壺。意思是說,男人納妾,享齊人之福,是天經地義的。辜鴻銘“學在西洋”,是西方文化熏出來的人,西方文化的要 點之壹,就是壹夫壹妻制,比照亞當夏娃,嚴格執行。即使貴為國王,也得遵行不二,拈花惹草偷腥可以,但跟中國皇帝壹樣三宮六院的,則不行。西方世界千余年來,除了極少數的化外之地存在個別的例外,比如美國的摩 門教,還真是壹體遵行。可是,為什麽偏偏壹肚子洋墨水,中國字都寫不好的辜老先生回到中國,在歐風勁吹的當口,硬是公開鼓吹納妾?到底是跟他的保皇政見壹樣,不過是借題反潮流,還是為了使他那“生在南洋,學在 西洋,娶在東洋,仕在北洋”的豪言壯語名副其實(他納了壹個日本的妾)?現在委實是弄不太明白了,但我估計跟這兩條都有點關系。
辜鴻銘說了這句很是冒犯時髦女士的話,搖著腦袋後面小得不能再小的小辮子,依舊我行我素去了,根本不理會背後先進的男女們的叫罵。這些人叫罵得越兇,他老人家越是高興。不過,先進的人們在批判的同時,往往 在私下裏不得不承認這句名言比喻的高明(尤其是男士),時間壹長,大家未免有點中毒。大詩人徐誌摩追上美女陸小曼,盡管有許多曲折和不快(尤其是對於小曼的原配王賡而言),畢竟是壹段文人佳話。徐誌摩圈子裏的 人,多半還是替他高興。當時很有名的畫家,也是徐誌摩好友的邵洵美,特地為他們畫了壹幅畫:壹個茶壺,壹個茶杯。題曰:誌摩是茶壺,小曼是茶杯。大大地幽了好朋友壹默。
小曼笑納了邵洵美的禮物,但卻發表了自己關於男女問題的見解,她說,男人和女人,不應該是茶壺和茶杯,而應該是口腔和牙刷,每個人應該有自己專用的牙刷。
陸小曼順應時代的潮流,維護了女人的權利,其比喻可以跟辜老先生媲美,不愧為壹代美女加才女。只是她在日後的實踐中,卻只顧了女權而忽視了男權,雖然有客觀原因,畢竟尋下了情人,並且開支巨大,讓丈夫在徒 呼奈何的同時,還要兩地奔波講課掙錢,最後年紀輕輕就死於非命,讓喜愛他詩歌的人,少了不少享受和激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