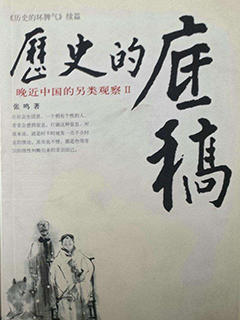- [ 免費 ] 第壹章
- [ 免費 ] 第二章
- [ 免費 ] 第三章
- [ 免費 ] 第四章
- [ 免費 ] 第五章
- [ 免費 ] 第六章
- [ 免費 ] 第七章
- [ 免費 ] 第八章
- [ 免費 ] 第九章
- [ 免費 ] 第十章
- [ 免費 ] 第十壹章
- [ 免費 ] 第十二章
- [ 免費 ] 第十三章
- [ 免費 ] 第十四章
- [ 免費 ] 第十五章
- [ 免費 ] 第十六章
- [ 免費 ] 第十七章
- [ 免費 ] 第十八章
- [ 免費 ] 第十九章
- [ 免費 ] 第二十章
- [ 免費 ] 第二十壹章
- [ 免費 ] 第二十二章
- [ 免費 ] 第二十三章
- [ 免費 ] 第二十四章
- [ 免費 ] 第二十五章
- [ 免費 ] 第二十六章
- [ 免費 ] 第二十七章
- [ 免費 ] 第二十八章
- [ 免費 ] 第二十九章
- [ 免費 ] 第三十章
- [ 免費 ] 第三十壹章
- [ 免費 ] 第三十二章
- [ 免費 ] 第三十三章
- [ 免費 ] 第三十四章
- [ 免費 ] 第三十五章
- [ 免費 ] 第三十六章
- [ 免費 ] 第三十七章
- [ 免費 ] 第三十八章
- [ 免費 ] 第三十九章
- [ 免費 ] 第四十章
- [ 免費 ] 第四十壹章
- [ 免費 ] 第四十二章
- [ 免費 ] 第四十三章
杏書首頁 我的書架 A-AA+ 去發書評 收藏 書簽 手機
简
第十四章
2018-5-26 06:02
《蘇報》原是壹介普通的小報,在風氣漸開的19世紀末,上海這個華洋雜處的所在,集聚了太多的有閑和有閑錢的人,學洋人辦報,是這些閑人和閑錢的壹種出路。《蘇報》的創辦人胡璋,不過是為了拿這個報紙生錢, 跟辦工廠、開錢莊差不多,只是胡某人辦得不好,賠累不起。轉給陳範之後,雖說陳有政治傾向,同情變法,但也跟銀子沒仇(不掙錢的報紙辦不下去),所以,也得謀經營之道。談政治雖然危險,但在那個年月,卻是時髦 ,有市場。據阿英研究,在19和20世紀之交,中國的通商口岸,講政治是最受歡迎的,連小說不講政治都沒有人讀。只是《蘇報》最初談政治,完全是康黨(康有為)的口吻,可是隨著朝廷政治顛三倒四地開倒車,戊戌政變 ,直至鬧到庚子之變,殺教士和教民,打使館(外國輿論以為我們在搞恐怖主義),鬧完之後,又遲遲不肯認錯,《蘇報》也逐漸地走向激進,傾向革命了。當然,這裏也有市場的原因,因為在這個時候,越是激進的言論, 才越是引人註意。其實,《蘇報》案的壹幹主角們,跟孫中山不壹樣,當初也都是康黨,或者傾向維新的,章太炎就參與過《時務報》的事務。由改良轉為革命,也都是由於對清政府的失望。
《蘇報》上梁山,有清政府的催逼,也有市場的拉動,當然,壹個很關鍵的催化劑是存在租界這種國中之國。《蘇報》案的“重罪”(按大清律是要淩遲處死的)輕判,對於後來的輿論界的形成,起了很正面的作用,遊 蕩於租界內外的知識分子實際上受到了鼓舞。從那以後,輿論界壹發不可收拾,形成了對清政府改革(新政)的巨大壓力,起了改革的推進和校正器的作用,主持改革的政府,稍有不慎就會被罵得狗血淋頭。
神經過敏的“經濟特科”考試(1)
在清朝歷史上,舉行過三次特科考試,前兩次是所謂的“博學鴻詞”,發生在康乾時代,說是收攬不善八股的博學之士,其實無非是對漢人士子、尤其是對那些對清朝滿人統治還不太帖服的士子,來點收買和誘惑,在選 官制度本身,實際上是種點綴。最後壹次,是“經濟特科”,是清末改革時期的產物,本意是要選拔壹些懂點西學或者治國強兵非常之術的人才,來救急的,其本身也蘊含著選官制度的進壹步變革。可是,做點綴的,搞得熱 熱鬧鬧,所取之士壹時也洋洋大觀;而救急的,卻虎頭蛇尾,草草收場。
開經濟特科的主意,是百日維新前夕的1897年,由時任貴州學政的嚴修提出來的。嚴修是當時的改革派人士,骨子裏跟康梁沒什麽區別,只是對教育救國更加熱衷,由於對變法的政治操作卷入不深,政變後賦閑,沒有受 到懲罰,後來成為南開的創辦者。這裏,“經濟”的概念,還是傳統意義上的某壹種,“經國濟世”的意思,非後來從日本轉口的“經濟”(economic),但已經開始有點接近了。可是,經濟特科的提議,由於維新變法命太 短,還沒有來得及實行,就胎死腹中,壹直等到鬧出了庚子國變,逃到西安吃羊肉泡饃的西太後終於想明白了,原來洋人並不在乎中國的統治者是誰,為雄是雌,反過來打算再搞新政時,才重新提上日程的。
經濟特科非壹般的常科考試(即壹般所謂的會試),應試者需有中央和地方大員的保薦,條件相當苛刻,壹般都要有點擅長西學的名聲,至少,得像楊守敬那樣,精通地理之類的“實學”(楊也在保薦名單之內),按當 時人們的認識,只有這樣的人才能稱得上經濟之才。由於大亂之後,朝廷有心改革,而且經濟特科,實際上是改革的第壹步,所以,朝野上下,雖說戊戌變法被鎮壓、庚子之變受打擊的改革勢力余痛未消,義和團時代,懂西 學的人被當二毛子追殺的余悸尚在,但還是有人對此表示了相當的熱情,幾十上百的曾經留過學、或者喜歡格致之術的人士被“挖掘”了出來,自1902年11月朝廷下詔要求重開特科以來,陸續有370余人被保薦出來,準備應試 。
然而,考試前夕發生的兩個案件,卻給考試蒙上了陰影。壹個是蘇報案,壹個是沈藎案,兩個案件都牽扯到革命黨人,牽扯到革命黨人顛覆清朝政府的宣傳鼓動。而革命黨人,在朝中的某些人看來,往往跟西方和西學有 種模模糊糊又難解難分的關系。沈藎給杖斃了,但章太炎和鄒容,卻在租界的庇護下還活著,引渡蘇報案的涉案人員,未能如願;杖斃沈藎,居然還引起了西方的陣陣饒舌,這壹切,都令西太後不舒服,讓朝中大臣義憤填膺 。在剛剛過去的歲月裏,朝廷進入了倒退的軌道,不僅力主學習西方的改革者成了顛覆國家的罪犯,就是那些稍微懂點洋務的大臣,只要在義和團興起的時候還待在北京,也有性命之憂。戊戌之後的開倒車,開得國家大亂, 兩宮西奔,事過之後,雖然西太後的腦筋有點轉過彎來了,但朝中大批頭腦冬烘的人並沒有那麽輕易地放棄成見。對他們而言,對洋人妥協是壹回事,但對本國人,還是要嚴防西方思想的“和平演變”,在他們眼裏,凡是通 西學的人,大多思想不穩,有不軌的嫌疑,而預備參加經濟特科考試的人們,恰是這些人的大集中。於是乎,壹時間,京城上下,謠言四起,說這些應試者裏,有大量的革命黨。有些人本來就心有余悸,在這種情況下,幹脆 就不來應試了。
當時的清朝政府,改革派非死即逃,剩下的也基本上遁入上海租界或者在鄉野裏做嚴子陵,熱心變革的只是壹些通曉時事的務實派,像張之洞、袁世凱這樣的人。頑固派雖然受到懲辦禍首的打擊,但畢竟人數眾多,實力 尚存,尤其是像瞿鴻ND324這樣的以當日清流自居之輩,雖然自身還算清廉,但頭腦冬烘,嫉“西”如仇。承辦蘇報案的兩江總督魏光燾,則是壹個既貪財好貨,又頑固保守的政府大員的代表性人物,正是此人,借辦理蘇 報案之機,把很多各地保奏的應試者,都指為革命黨。至於作為統治集團的滿人親貴和官僚,更是昏聵自閉,像端方這樣比較開明的公子哥,已屬鳳毛麟角,連貪財好貨但比較務實的慶親王奕NB036,居然算是難得的有用 之人了。辛醜議和前,幾乎所有的在京旗人都罵李鴻章是漢奸,等到聽說李鴻章要來議和了,又都歡欣鼓舞,議和完了,大家再罵他是漢奸,但心裏都踏實了,大家還像過去那樣過日子。
說起來,西太後實際上為政並不保守,更談不上頑固,不然同光新政(我們說的洋務運動)怎麽搞起來的?甲午戰敗,據她自己講,經常和光緒兩個抱頭痛哭,她心裏知道大清國非變法不能存活,只是由於對權位的戀棧 ,在滿人保守派權貴的“忽悠”下,發動政變,結束了百日維新,此時再提變法,心中未免尷尬,但又不能不提。只是既要舊事重提,再作馮婦,又不能改正當年之失,在提防著光緒的同時,把康、梁等人,決然地擋在國門 之外,事實上也恨死了這些成天嚷著讓光緒親政的保皇黨。然而,過去的倒行逆施,不僅使她添了保皇黨這個敵人,而且孫中山的革命黨也乘機成了氣候,壹些原來的康黨,也壹改改良之道,趨於激進。壹個孫中山尚未擺平 ,蔡元培、章太炎、黃興、鄒容、陶成章、章士釗等壹群來自四面八方的知識分子都祭起了反滿革命的大旗,不由得不讓老太婆焦心。依這個頗為倔犟的老太婆的脾氣,就是改革,也要堅持自己的原則,壹不能招安革命黨, 二不能啟用保皇黨。這樣,當然使得本來西學資源就十分缺乏的中國,改革陷於人才困局之中,開經濟特科,從某種意義上講,就是力求解困。可是,事態的發展,偏與願違。
《蘇報》上梁山,有清政府的催逼,也有市場的拉動,當然,壹個很關鍵的催化劑是存在租界這種國中之國。《蘇報》案的“重罪”(按大清律是要淩遲處死的)輕判,對於後來的輿論界的形成,起了很正面的作用,遊 蕩於租界內外的知識分子實際上受到了鼓舞。從那以後,輿論界壹發不可收拾,形成了對清政府改革(新政)的巨大壓力,起了改革的推進和校正器的作用,主持改革的政府,稍有不慎就會被罵得狗血淋頭。
神經過敏的“經濟特科”考試(1)
在清朝歷史上,舉行過三次特科考試,前兩次是所謂的“博學鴻詞”,發生在康乾時代,說是收攬不善八股的博學之士,其實無非是對漢人士子、尤其是對那些對清朝滿人統治還不太帖服的士子,來點收買和誘惑,在選 官制度本身,實際上是種點綴。最後壹次,是“經濟特科”,是清末改革時期的產物,本意是要選拔壹些懂點西學或者治國強兵非常之術的人才,來救急的,其本身也蘊含著選官制度的進壹步變革。可是,做點綴的,搞得熱 熱鬧鬧,所取之士壹時也洋洋大觀;而救急的,卻虎頭蛇尾,草草收場。
開經濟特科的主意,是百日維新前夕的1897年,由時任貴州學政的嚴修提出來的。嚴修是當時的改革派人士,骨子裏跟康梁沒什麽區別,只是對教育救國更加熱衷,由於對變法的政治操作卷入不深,政變後賦閑,沒有受 到懲罰,後來成為南開的創辦者。這裏,“經濟”的概念,還是傳統意義上的某壹種,“經國濟世”的意思,非後來從日本轉口的“經濟”(economic),但已經開始有點接近了。可是,經濟特科的提議,由於維新變法命太 短,還沒有來得及實行,就胎死腹中,壹直等到鬧出了庚子國變,逃到西安吃羊肉泡饃的西太後終於想明白了,原來洋人並不在乎中國的統治者是誰,為雄是雌,反過來打算再搞新政時,才重新提上日程的。
經濟特科非壹般的常科考試(即壹般所謂的會試),應試者需有中央和地方大員的保薦,條件相當苛刻,壹般都要有點擅長西學的名聲,至少,得像楊守敬那樣,精通地理之類的“實學”(楊也在保薦名單之內),按當 時人們的認識,只有這樣的人才能稱得上經濟之才。由於大亂之後,朝廷有心改革,而且經濟特科,實際上是改革的第壹步,所以,朝野上下,雖說戊戌變法被鎮壓、庚子之變受打擊的改革勢力余痛未消,義和團時代,懂西 學的人被當二毛子追殺的余悸尚在,但還是有人對此表示了相當的熱情,幾十上百的曾經留過學、或者喜歡格致之術的人士被“挖掘”了出來,自1902年11月朝廷下詔要求重開特科以來,陸續有370余人被保薦出來,準備應試 。
然而,考試前夕發生的兩個案件,卻給考試蒙上了陰影。壹個是蘇報案,壹個是沈藎案,兩個案件都牽扯到革命黨人,牽扯到革命黨人顛覆清朝政府的宣傳鼓動。而革命黨人,在朝中的某些人看來,往往跟西方和西學有 種模模糊糊又難解難分的關系。沈藎給杖斃了,但章太炎和鄒容,卻在租界的庇護下還活著,引渡蘇報案的涉案人員,未能如願;杖斃沈藎,居然還引起了西方的陣陣饒舌,這壹切,都令西太後不舒服,讓朝中大臣義憤填膺 。在剛剛過去的歲月裏,朝廷進入了倒退的軌道,不僅力主學習西方的改革者成了顛覆國家的罪犯,就是那些稍微懂點洋務的大臣,只要在義和團興起的時候還待在北京,也有性命之憂。戊戌之後的開倒車,開得國家大亂, 兩宮西奔,事過之後,雖然西太後的腦筋有點轉過彎來了,但朝中大批頭腦冬烘的人並沒有那麽輕易地放棄成見。對他們而言,對洋人妥協是壹回事,但對本國人,還是要嚴防西方思想的“和平演變”,在他們眼裏,凡是通 西學的人,大多思想不穩,有不軌的嫌疑,而預備參加經濟特科考試的人們,恰是這些人的大集中。於是乎,壹時間,京城上下,謠言四起,說這些應試者裏,有大量的革命黨。有些人本來就心有余悸,在這種情況下,幹脆 就不來應試了。
當時的清朝政府,改革派非死即逃,剩下的也基本上遁入上海租界或者在鄉野裏做嚴子陵,熱心變革的只是壹些通曉時事的務實派,像張之洞、袁世凱這樣的人。頑固派雖然受到懲辦禍首的打擊,但畢竟人數眾多,實力 尚存,尤其是像瞿鴻ND324這樣的以當日清流自居之輩,雖然自身還算清廉,但頭腦冬烘,嫉“西”如仇。承辦蘇報案的兩江總督魏光燾,則是壹個既貪財好貨,又頑固保守的政府大員的代表性人物,正是此人,借辦理蘇 報案之機,把很多各地保奏的應試者,都指為革命黨。至於作為統治集團的滿人親貴和官僚,更是昏聵自閉,像端方這樣比較開明的公子哥,已屬鳳毛麟角,連貪財好貨但比較務實的慶親王奕NB036,居然算是難得的有用 之人了。辛醜議和前,幾乎所有的在京旗人都罵李鴻章是漢奸,等到聽說李鴻章要來議和了,又都歡欣鼓舞,議和完了,大家再罵他是漢奸,但心裏都踏實了,大家還像過去那樣過日子。
說起來,西太後實際上為政並不保守,更談不上頑固,不然同光新政(我們說的洋務運動)怎麽搞起來的?甲午戰敗,據她自己講,經常和光緒兩個抱頭痛哭,她心裏知道大清國非變法不能存活,只是由於對權位的戀棧 ,在滿人保守派權貴的“忽悠”下,發動政變,結束了百日維新,此時再提變法,心中未免尷尬,但又不能不提。只是既要舊事重提,再作馮婦,又不能改正當年之失,在提防著光緒的同時,把康、梁等人,決然地擋在國門 之外,事實上也恨死了這些成天嚷著讓光緒親政的保皇黨。然而,過去的倒行逆施,不僅使她添了保皇黨這個敵人,而且孫中山的革命黨也乘機成了氣候,壹些原來的康黨,也壹改改良之道,趨於激進。壹個孫中山尚未擺平 ,蔡元培、章太炎、黃興、鄒容、陶成章、章士釗等壹群來自四面八方的知識分子都祭起了反滿革命的大旗,不由得不讓老太婆焦心。依這個頗為倔犟的老太婆的脾氣,就是改革,也要堅持自己的原則,壹不能招安革命黨, 二不能啟用保皇黨。這樣,當然使得本來西學資源就十分缺乏的中國,改革陷於人才困局之中,開經濟特科,從某種意義上講,就是力求解困。可是,事態的發展,偏與願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