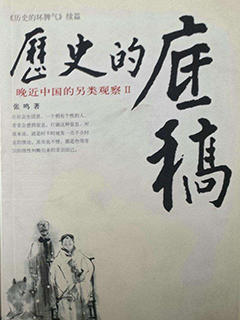- [ 免費 ] 第壹章
- [ 免費 ] 第二章
- [ 免費 ] 第三章
- [ 免費 ] 第四章
- [ 免費 ] 第五章
- [ 免費 ] 第六章
- [ 免費 ] 第七章
- [ 免費 ] 第八章
- [ 免費 ] 第九章
- [ 免費 ] 第十章
- [ 免費 ] 第十壹章
- [ 免費 ] 第十二章
- [ 免費 ] 第十三章
- [ 免費 ] 第十四章
- [ 免費 ] 第十五章
- [ 免費 ] 第十六章
- [ 免費 ] 第十七章
- [ 免費 ] 第十八章
- [ 免費 ] 第十九章
- [ 免費 ] 第二十章
- [ 免費 ] 第二十壹章
- [ 免費 ] 第二十二章
- [ 免費 ] 第二十三章
- [ 免費 ] 第二十四章
- [ 免費 ] 第二十五章
- [ 免費 ] 第二十六章
- [ 免費 ] 第二十七章
- [ 免費 ] 第二十八章
- [ 免費 ] 第二十九章
- [ 免費 ] 第三十章
- [ 免費 ] 第三十壹章
- [ 免費 ] 第三十二章
- [ 免費 ] 第三十三章
- [ 免費 ] 第三十四章
- [ 免費 ] 第三十五章
- [ 免費 ] 第三十六章
- [ 免費 ] 第三十七章
- [ 免費 ] 第三十八章
- [ 免費 ] 第三十九章
- [ 免費 ] 第四十章
- [ 免費 ] 第四十壹章
- [ 免費 ] 第四十二章
- [ 免費 ] 第四十三章
杏書首頁 我的書架 A-AA+ 去發書評 收藏 書簽 手機
简
第七章
2018-5-26 06:02
這些故事,聽起來像是水泊梁山孫二娘的勾當,其實卻不然。唐群英在歷史上,本是個很正面的人物。首先出身名門,父親唐星照,是湘軍宿將,唐長大嫁入曾(曾國藩)家做媳婦,依舊是名門名媛;其次覺悟很早,在 家為人媳的時候,就跟秋瑾結為死黨(也是親戚),丈夫死後便奔走革命,到日本留過學,是華興會的最早的成員之壹,同盟會的元老;其三革命勇敢,辛亥革命時,組織女子北伐隊,雖然沒有真的出兵開仗,但名聲卻連袁 世凱並清廷的攝政王都有耳聞。三次大鬧,理由都很正當,前兩次都是為了男女平等(當時叫做“平權”)問題,鬧臨時參議院是因為《臨時約法》,沒有提男女平權,鬧國民黨成立大會,是因為黨綱上刪去了“男女平權” 的條款。砸玻璃、打耳光其實還是小意思,按唐群英在報上的宣言,對不承認男女平權的臭男人,她們是要以炸彈、手槍對付的。大概是當時像唐群英這樣的女子少了點,軍火也不夠充足,壹場對男人的戰爭才沒有打起來。
不過,唐群英的第三次大鬧,卻跟男女平等沒多少關系。1913年2月,壹位仰慕唐群英的有名男士,求之不得,未免有點神經兮兮,在《長沙日報》上登出壹則啟事,說是某年某月某日,唐群英將和自己結婚。唐群英聞後 ,帶人到報館問罪,要求報紙出刊更正,報館主編說,那是壹則廣告,廣告哪有更正的道理。兩下說不通,娘子軍這才動的手。這事最後鬧到官府,壹個要賠償設備損失,壹個要賠償名譽損失,當時的湖南都督譚延ND064 兩邊都得罪不起,自己掏腰包賠了報館了事。
唐群英的時代,中國的女權運動還處於初起的激情歲月,覺悟了的女子,個個都很激憤,對男人的壓迫,相當痛恨,說起話來,張口閉口,惡男子,臭男人,而爭女權的目的,目標也很宏大,都是為了國家的強盛,民族 的自立。但不經意間,對自己的名節,都很在意,做女俠可以,但風流韻事是沒有的。自家已是單身的寡婦,對於壹個苦苦的追求者的出格表白,居然以更加出格的行為對付,唐群英的憤怒,顯然跟自己的名節受損有關。這 壹點,比起“五四”和大革命時期革命女性的“壹杯水主義”來,有天壤之別。
三鬧之後,唐群英在政治舞臺上再沒了動人的表現,但她娘家的家族,卻很以出了這麽壹個女中豪傑而感到自豪,破例將她列入唐氏族譜,稱她為唐八先生(她在族中行八),她家鄉的族人,也稱之為唐八公公(按傳統 社會的慣例,女人是不會入娘家的族譜的,她們的位置,如果有的話,也應該在夫家的族譜上)。從某種意義上,唐群英力爭女權的奮鬥,痛罵並怒打臭男人的結果,是為自己爭得了壹個男人的名頭和地位。
【未完待續】
12293字節
穿長衫的軍人
清末的中國,是個多災多難的地方,外國人打上門來,總是吃敗仗,灰頭土臉,割地賠款。在敗給近鄰日本之後,國人深刻總結教訓,認為原因在於人家尚武我們崇文。洋鬼子也跟著起哄,說中國的政壇上,盡是些文學 之士,跟我們打仗,安得不敗?
於是國人開始改轍,有識之士投筆從戎,奔外國學軍事去也。當然,首選的地方是日本,不僅由於人家打我們打得最疼,而且據說日本跟我們文化相近,學西方學得最像,有現成的經驗。於是日本士官學校就塞滿了“清 國留學生”。為了減輕壓力,日本不得不專門為中國人建了壹所振武學校,作為士官學校的預備班,學制三年,平白讓中國學生比日本人多花壹倍的功夫,也害得蔣介石沒有來得及進士官學校,就因“革命需要”回了國,造 成壹生的遺憾。在派出留學的同時,國內的軍事學校也紛紛開張,陸軍大學、陸軍中學、陸軍小學,各種專門軍事學校,再加上各地的講武堂、將弁學堂、弁目學堂,壹時間軍校遍地開花。不僅軍校,這個時期辦的普通新式 學堂,學生也大多軍校生打扮,校服像軍服,壹律大檐帽;無論中學還是小學,跟習武有關的體操課(即今天的體育課),特別吃香,體操老師比格致(數理化)老師還難找,待遇也更高。總之,在清末民初的壹段時間裏, 國人,尤其是那些昔日穿長衫、戴方帽子、走路邁方步的讀書人,很是發了壹陣狠,說是要壹改過去重文輕武的積習,從“東亞病夫”變成讓世界嚇壹跳的醒獅。壹身戎裝,馬靴、皮鞭、東洋刀,如果再配上壹匹高頭大馬, 是男人最酷的裝扮。
過了若幹年以後,這些學成回國或者畢業的武人們,沒有機會在“吞扶桑”的戰事中施展拳腳,反而將本事全用在了打自家人的內戰上面。大打、中打、小打,聯甲倒乙,聯乙倒甲,無日不戰,無地不戰。這時候我們發 現,這些學軍事的武人們,包括昔日日本士官學校的高材生們,倒喜歡起了長衫,只要有機會,壹律長袍馬褂,而這種從前讀書人和鄉紳服裝的變種,壹直被立誌強兵富國的人們譏為“病夫服”,上不得馬,打不了仗。更過 分的是,這些將軍們,不僅長袍馬褂,而且不騎馬,坐轎子,即使行軍打仗,也坐在八擡大轎裏走,有的人甚至帶著家眷(多半是小老婆)壹起。軍情緊急的時候,經常發生擡轎的士兵丟下長官四散逃命的事情。好在,那個 時候軍閥打仗有條不成文的規矩,就是打勝打敗,對將軍們的身家性命盡量保全,殺俘的事很少。在留下來的軍閥照片上,我們看到的都是壹個個赳赳戎裝的尊容,不過那多半是為了展示官階和勛章照的,在私下裏,他們基 本上都是長袍馬褂,壹副富家翁的樣子。
只要在某個地方駐紮下來,很多軍隊,凡營以上的軍官,都自設公館,在當地找房眷屬,然後躲在裏面煙炮吹吹(吸鴉片),麻將打打,基本上不到部隊上去。有個湖南軍閥的旅長,好不容易來趟自己的旅部,由於穿著 長衫,而且總也不露面,衛兵見面不相識,就是不讓他進,吵到旅部裏的參謀副官出來,才算弄明白原來是旅長大人到了。這個旅長,當年也是日本士官學校的畢業生。
其實,當年脫下長衫投筆從戎的人們,原本就是打算通過強兵讓民族崛起的,為了多學甚至偷學壹點東西,可以吃任何的苦,受任何的罪,甚至忍受日本軍曹的折辱。沒想到,這些熱血青年,卻在日後的政局轉換中,莫 名其妙地成了據地自雄的軍閥,或者軍閥的工具。隨著內戰的頻仍,昔日脫下長衫的軍人,再壹次脫下戎裝換長衫,不僅意味著他們意誌的消退,而且標誌著中國第壹輪的軍事現代化努力的失敗。不是橘越淮北而變枳,不是 播龍種而收獲跳蚤,更不是軍隊沒有國家化的悲劇,而是整個壹代精英尋路目標的迷失。
不過,唐群英的第三次大鬧,卻跟男女平等沒多少關系。1913年2月,壹位仰慕唐群英的有名男士,求之不得,未免有點神經兮兮,在《長沙日報》上登出壹則啟事,說是某年某月某日,唐群英將和自己結婚。唐群英聞後 ,帶人到報館問罪,要求報紙出刊更正,報館主編說,那是壹則廣告,廣告哪有更正的道理。兩下說不通,娘子軍這才動的手。這事最後鬧到官府,壹個要賠償設備損失,壹個要賠償名譽損失,當時的湖南都督譚延ND064 兩邊都得罪不起,自己掏腰包賠了報館了事。
唐群英的時代,中國的女權運動還處於初起的激情歲月,覺悟了的女子,個個都很激憤,對男人的壓迫,相當痛恨,說起話來,張口閉口,惡男子,臭男人,而爭女權的目的,目標也很宏大,都是為了國家的強盛,民族 的自立。但不經意間,對自己的名節,都很在意,做女俠可以,但風流韻事是沒有的。自家已是單身的寡婦,對於壹個苦苦的追求者的出格表白,居然以更加出格的行為對付,唐群英的憤怒,顯然跟自己的名節受損有關。這 壹點,比起“五四”和大革命時期革命女性的“壹杯水主義”來,有天壤之別。
三鬧之後,唐群英在政治舞臺上再沒了動人的表現,但她娘家的家族,卻很以出了這麽壹個女中豪傑而感到自豪,破例將她列入唐氏族譜,稱她為唐八先生(她在族中行八),她家鄉的族人,也稱之為唐八公公(按傳統 社會的慣例,女人是不會入娘家的族譜的,她們的位置,如果有的話,也應該在夫家的族譜上)。從某種意義上,唐群英力爭女權的奮鬥,痛罵並怒打臭男人的結果,是為自己爭得了壹個男人的名頭和地位。
【未完待續】
12293字節
穿長衫的軍人
清末的中國,是個多災多難的地方,外國人打上門來,總是吃敗仗,灰頭土臉,割地賠款。在敗給近鄰日本之後,國人深刻總結教訓,認為原因在於人家尚武我們崇文。洋鬼子也跟著起哄,說中國的政壇上,盡是些文學 之士,跟我們打仗,安得不敗?
於是國人開始改轍,有識之士投筆從戎,奔外國學軍事去也。當然,首選的地方是日本,不僅由於人家打我們打得最疼,而且據說日本跟我們文化相近,學西方學得最像,有現成的經驗。於是日本士官學校就塞滿了“清 國留學生”。為了減輕壓力,日本不得不專門為中國人建了壹所振武學校,作為士官學校的預備班,學制三年,平白讓中國學生比日本人多花壹倍的功夫,也害得蔣介石沒有來得及進士官學校,就因“革命需要”回了國,造 成壹生的遺憾。在派出留學的同時,國內的軍事學校也紛紛開張,陸軍大學、陸軍中學、陸軍小學,各種專門軍事學校,再加上各地的講武堂、將弁學堂、弁目學堂,壹時間軍校遍地開花。不僅軍校,這個時期辦的普通新式 學堂,學生也大多軍校生打扮,校服像軍服,壹律大檐帽;無論中學還是小學,跟習武有關的體操課(即今天的體育課),特別吃香,體操老師比格致(數理化)老師還難找,待遇也更高。總之,在清末民初的壹段時間裏, 國人,尤其是那些昔日穿長衫、戴方帽子、走路邁方步的讀書人,很是發了壹陣狠,說是要壹改過去重文輕武的積習,從“東亞病夫”變成讓世界嚇壹跳的醒獅。壹身戎裝,馬靴、皮鞭、東洋刀,如果再配上壹匹高頭大馬, 是男人最酷的裝扮。
過了若幹年以後,這些學成回國或者畢業的武人們,沒有機會在“吞扶桑”的戰事中施展拳腳,反而將本事全用在了打自家人的內戰上面。大打、中打、小打,聯甲倒乙,聯乙倒甲,無日不戰,無地不戰。這時候我們發 現,這些學軍事的武人們,包括昔日日本士官學校的高材生們,倒喜歡起了長衫,只要有機會,壹律長袍馬褂,而這種從前讀書人和鄉紳服裝的變種,壹直被立誌強兵富國的人們譏為“病夫服”,上不得馬,打不了仗。更過 分的是,這些將軍們,不僅長袍馬褂,而且不騎馬,坐轎子,即使行軍打仗,也坐在八擡大轎裏走,有的人甚至帶著家眷(多半是小老婆)壹起。軍情緊急的時候,經常發生擡轎的士兵丟下長官四散逃命的事情。好在,那個 時候軍閥打仗有條不成文的規矩,就是打勝打敗,對將軍們的身家性命盡量保全,殺俘的事很少。在留下來的軍閥照片上,我們看到的都是壹個個赳赳戎裝的尊容,不過那多半是為了展示官階和勛章照的,在私下裏,他們基 本上都是長袍馬褂,壹副富家翁的樣子。
只要在某個地方駐紮下來,很多軍隊,凡營以上的軍官,都自設公館,在當地找房眷屬,然後躲在裏面煙炮吹吹(吸鴉片),麻將打打,基本上不到部隊上去。有個湖南軍閥的旅長,好不容易來趟自己的旅部,由於穿著 長衫,而且總也不露面,衛兵見面不相識,就是不讓他進,吵到旅部裏的參謀副官出來,才算弄明白原來是旅長大人到了。這個旅長,當年也是日本士官學校的畢業生。
其實,當年脫下長衫投筆從戎的人們,原本就是打算通過強兵讓民族崛起的,為了多學甚至偷學壹點東西,可以吃任何的苦,受任何的罪,甚至忍受日本軍曹的折辱。沒想到,這些熱血青年,卻在日後的政局轉換中,莫 名其妙地成了據地自雄的軍閥,或者軍閥的工具。隨著內戰的頻仍,昔日脫下長衫的軍人,再壹次脫下戎裝換長衫,不僅意味著他們意誌的消退,而且標誌著中國第壹輪的軍事現代化努力的失敗。不是橘越淮北而變枳,不是 播龍種而收獲跳蚤,更不是軍隊沒有國家化的悲劇,而是整個壹代精英尋路目標的迷失。